一、哈贝马斯的生平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是本世纪6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文化科学界崭露头角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今天他仍被公认为“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历史科学、心理学等领域中有着深厚的造诣,而且还是这些学科中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最有成就的鼓动家’;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不仅在联邦德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巨大影响,被称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而且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哲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雷克斯认为,哈贝马斯的造诣之深可与黑格尔相媲美;彼得·威尔比(Peter Wilby)则直接称哈贝马斯是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正是由于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贡献和巨大影响,1974年,他荣获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的黑格尔奖金;1975年,联邦德国达尔姆斯达特市德国语言和文学科学院授予他弗洛伊德科学散文奖;1980年,荣获法兰克福阿多尔诺奖金;1980年,美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称号;1981年,匈牙利科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
哈贝马斯出生于1929年6月18日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市镇—古玛斯巴赫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祖父是一位神学院院长;父亲是当地工商联合会会长。这样一个家庭,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并不引人注目,它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态度总的说来是顺从,是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哈贝马斯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及其发动的野蛮和残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但是,哈贝马斯那时对于法西斯在德国本土以及在其他许多国家犯下的累累罪行并不关心和了解。
1945年,法西斯德国投降时,哈贝马斯正好16岁。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谈到:那时,我从广播上听到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争贩子们的审判中,从电视上看到的揭露希特勒匪徒在集中营里的幕虐行为中,才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这段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后来的思想。这段经历促进了他的政治意识的萌发。他开始对法西斯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开始认识到,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是一种罪恶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为德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开始新的坐活而兴高采烈,内心感到这一重大转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这种认识决定了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态度。
1945年法西斯的垮台,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从前被查禁和被付之一炬的书籍,又重新出现在社会上。这些书籍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哈贝马斯,促使他怀着幼稚的好奇的兴趣在家乡的小镇图书馆里阅读着他能够接触到的多种书籍;他也如饥似渴地在德国共产党开办的书店里阅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
1949年,哈贝马斯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德国文学和经济学。这年9月,阿登纳领导的第一届联邦政府成立。然而,这个政府竟允许它的内阁成员中有坚持纳粹思想的人。这件事使哈贝马斯对这个政府是不是民主政府,以及到底能否同纳粹思想彻底决裂产生了怀疑。这件事同时也加深了他对实行社会民主和为此而进行斗争的认识。哈贝马斯当时的这种认识只不过是一种厌战的和平主义者的自发的感性认识。所以,在学习哲学的初期,他曾认为哲学同政治是没有相互依赖关系的。1953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只字未改地发表了他1935年在弗赖堡大学任教时所作的报告《形而上学引论》。海德格尔的这一举动使哈贝马斯深为震惊。这使他开始认识到:哲学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除非哲学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多种政治事件置之不理。这是哈贝马斯反对纳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53年,哈贝马斯由苏黎士大学转入波恩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卢卡奇在书中所阐述的物化理论以及其他多种观点,都使他激动不已。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阅读情况时说,罗维特(Karl Lowith)和卢卡奇是他学习和研究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引路人。
1955年,他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代表人物针对现代社会发展阐述的辩证理论,以及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所阐明的思想,使他感到新奇。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物化学说,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他后来的理论发展曾产生了推动作用。可以说,他从这个时期开始,把哲学兴趣同对实际政治兴趣结合了起来,并随之对现实政洽产生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1961年,他的教授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马堡大学沃尔夫冈·阿本特欧特教授(Wolfgong Abendroth)这里获得了通过。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964年,哈贝马斯作为副教授执教于海德堡大学,同年下半年,他来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71年。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加上他经常向学生讲演,同他们一起讨论,回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因而深受学生的欢迎和爱戴,讲堂内总是座无虚席。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了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运动初期,哈贝马斯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当‘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时,我同阿本特欧特等几位教授一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联合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一个老年战斗队”。但是,不久他就同激进的学生运动发生了分歧,其根本原因是双方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不同估计和分析。在左派学生领导人看来,工人运动的时代又到来了,革命爆发即在眼前。因此对联邦德国议会中的某些法西斯化的趋势,能够并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暴力行动。于是,学生运动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规模愈来愈大,斗争愈来愈激烈。他们举行游行示威,冲课堂,向教授们扔臭鸡蛋和西红柿;学生联合会还计划召开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学生会议,并在整个德国举行游行示威,直至到已由警察占领着的大学举行示威,占领大学院系和一些研究机构。尽管哈贝马斯认为,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不民主、不自由的现象,但这个社会制度总起来说,是比较优越的,政治、经济的形势也是稳定的。因此对于议会中存在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有说服力的分析或启蒙形式来解决,而不能使用暴力。他指责学生们的过激行动,甚至公开谴责他们是“左派法西斯”,而学生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1968年12月,左派学生夺了他的权--占领了他当时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近10天。双方冲突甚至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于1971年终于离开了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和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和这个学会的学部委员。
在普朗克学会任职期间,他常因人事和行政工作中的问题同科学和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尔·弗利德利希·魏茨泽克××不断,于1981年4月辞去该研究所所长职务,到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致力于他的研究工作。
1983年,他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至199年退休。
二、哈贝马斯的创作
哈贝马斯是位多产作家。从他开始学术生涯的60年代初起,到今天的近40年里,他发表的著作有30多部。
哈贝马斯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60年代初到1968年他与学生运动彻底决裂;二,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三,80年代初,特别是他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至今。当然,这三个阶段的界限并非一目了然;他的学术思想是相互连接和交叉发展的。
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在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思想影响下,抱着浓厚的政治兴趣,把哲学兴趣和对现实政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用批判的眼光揭示、分析和抨击他所看到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和事物。因而,他这个阶段的著作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为了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现象及其危险发展趋势的关注,他在其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热情赞扬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律制度和舆论制度所起的政治功能以及其所依赖的自由和理性原则,并明确指出:19世纪下半叶以后,公众的喉舌—报纸和大众宣传工具,逐渐被少数人,被社会团体、政党,最后被D9家所掌握和垄断,成了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工具;公众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媒介物,从而也丧失了他们过去享有的一切权利。他们原来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现在被以集体利益为幌子,实际上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团体和政党所代替;原来他们手中的工具,现在倒过来成了政党的工具。公众裁决愈来愈成了行政裁决,并且,行政裁决对于公民来说,越来越成了看不见的东西和不能批评的东西。有时国家也把公众吸引到它的权力管理之中.但这往往只是为了达到为政权叫好的目的。劳动者能够作出的决断,是在官方经济决策机关和政治裁决机关的影响下做出的。而政府之所以对劳动者感兴趣,是因为政治权力的贯彻还依赖于他们的选票,其目的是加强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在选举中的地位,它们根本不理睬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性。曾经具有批评权利的公众,现在成了被愚弄的公众;政党召开的群众大会也只是一种宣传活动,参加大会的群众也只能扮演一种没有报酬的跑龙套的角色。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还有:《大学生与政治》、《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第二阶段的特点,按照联邦德国一些评论家的说法,政治上属倒退,理论上是悲观失望,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某些墓本原理,为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作论证。这在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中表述得甚为明显。
哈贝马斯本人则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古典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杜会,而是进入了由“国家管理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这种变化,人们不应该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去运用马克恩主义的某些墓本范畴,而应根据情况重新考虑,对它们作出新的解释。他认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对待一种从某种方面需要修正,但它的鼓舞人的潜力永远没有枯渴的理论的正常态度”。所以,他在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之后指出,在这个社会里,由于科学技术直接运用于生产,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实际上决定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了“独立的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马克恩本人在考察中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愈来愈不重要”,“.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不存在了”。在此基础上,他对马克思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重新作了解释。他在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时,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也作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经济危机仍然发生,但是这种危机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加以控制;发展所遇到的干扰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排除,还可以越过政治系统放到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得到解决。
他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1973年)、《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年)、《交往行动的理论》(1981),等等。
80年代后,特别是从1983年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直到1994年退休至今,可以说是他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关心人的道德意识发展和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建立,或者说,社会稳定问题.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论题。
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墓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对话应以相互谅解为目的,而不能以追求自己取得成果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的人,是不会开诚布公地同他的伙伴进行诚实对话的,是不会同对方进行协调行动的.因此也就无法同对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相互谅解就是亲善”。“每个人对他人都应怀着普遍的、团结互助的责任心,……团结他人,即把他人视作我们中的一分子,是我们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责任。有道德的共同体,仅仅是通过铲除歧视人和给人带来痛苦的消极观念,以及把那些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包容在相互关怀中建立起来的……包容他人,不是把他人融入自身,更不是排斤他人。没有差别地尊重每个人,也应该是尊重另一个国家的人或是有自身差异的不同民族的人”。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还有:《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1983年)、《现代哲学对话》(1985年》、《一种清算灾难的形式》(1987年)、《后潜而上学思维》( 1988年)、《追补的革命》(1991年)、《作为未来的过去》(1991年)、《事实与价值》(1992年)、《对话伦理学解说》(1992年)、《包容他人》(1996年)等。
三、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理论框架
《认识与兴趣》是哈贝马斯专门论述认识论问题的一本重要哲学专著。它的基本论点首先见诸于1965年6月他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职务时发表的题为“认识与兴趣”的演讲(以下简称“演讲”)。在此后的三年里,他结合在海德堡大学讲授的课题: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历史主义和他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研究,写成了这部专著。
1968年,这部专著问世后,在德国以及欧美一些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快被译为英、法、俄、日、南斯拉夫和波兰文,并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到1995年止,该书在德国再版14次,成了一本常销不衰的书。
认识论问题,是近代哲学论争的一个中心问题。哈贝马斯认为,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怎样才能有可靠的认识这么一个问题。他在该书中正是抓住了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认识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他认为,康德提出的先验逻辑问题,使认识论有了起点,使其形成为一个独特的领域。但由于康德的认识批判把科学作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基础,揭示的是反思的先验范畴,因而他的先验哲学的前提和假设没有能经得住黑格尔对它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使认识论前进了一步。在黑格尔看来,先验的反思不是绝对的开始,而是依款于某种先已存在的东西,因为任何形式的认识都只能形成于一个练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借助于语言、劳动和统治(人的相互作用)完成的。然而,黑格尔强调的绝对知识和绝对精神哲学,“削弱了黑格尔批判康德的力量”。否认了认识批判的反思的合法性,从而取消了认识论。“同一性哲学的基本假设……妨碍了黑格尔明确地把认识批判贯彻到底”。
哈贝马斯赞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有关理论,即人的认识不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的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自我,也不是绝对精神,而是有驱体的、能劳动的主体。这个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在向自然界以及其他人的、不断变换形式的交往中积累起来的。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开辟了一条对认识的主体进行反思的道路。这条道路既避免了康德的先验批判的个体的和非历史的局限性,使康德提出的认识的主体的综合仅仅成了人的感性活动的苍白无力的反思,又避免了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的唯心主义的极端性。
然而,哈贝马斯又同时认为,“在马克思的阐述中,尽管包含着构成彻底认识批判的一切要素,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没有用认识论的观点来构想可以用唯物主义来理解的类的历史”。
哈贝马斯明确提出,自19世纪中叶以后,认识论已被知识学所代替,因此,他以专门的篇章批判了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指出,实证主义的观点否认哲学反思的价值,它不再研究认识的条件和意义,用现代科学的事实代替认识论,并试图用唯科学论的知识学来代替认识批判的反思,其后果则是排除了科学对自身的反思,也排除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现象进行自我反思的研究,妨碍了人们用一种对社会分析来说是恰当的方式去研究人的行为。
他在论述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解释学时,指出了他们在认识论上的贡献和问题。他认为,这两位思想家对科学都作了彻底的自我反思,但却都是错误的反思。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实证主义的束缚,所以也就没有能实现他们自己所开创的克服实证主义的可能性。他写道:“皮尔士和狄尔泰都触及到了认识的兴趣基础。但都没有对这种基础本身加以反思。他们未能形成指导认识的兴趣的概念,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概念所追求的东西。他们诚然从生活联系中分析了研究逻辑的基础,但是,似乎都只是在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范围内,即在作为形成过程来理解的类的历史概念内,把经验分析科学和解释学的基本方向当作指导认识的兴趣……因为皮尔士和狄尔泰没有把他们的方法理解为科学的自我反思(科学就是自我反思),所以他们没有得出认识和兴趣的统一观”。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识的兴趣这一概念,并以这一概念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了认识与兴趣在自然科学中和精神科学中的联系,揭示了被实证主义丢弃了的认识论的反思维度。
那么,哈贝马斯所理解的认识和兴趣的含义是什么?他是如何构建他的认识论的框架的呢?
哈贝马斯认为,认识既不是生物适应不断变化的环瑰的一种单纯的工具,又不是纯粹的理性生物的一种活动,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性的特殊的范畴。它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工具和创造新生活的手段。它是主体(人)借助于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在使用技术占有自然的进程中,在把握人的共性的进程中完成的。人类离开了对自然界,对人际关系的不断的新的认识,就无法存在下去。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彻底的认识论必须具有社会理论的形式.因为无论是认识的主体,还是被认识的客体,离开了社会历史的联系,都是不可想象的。
哈贝马斯所说的兴趣又是什么呢?对此他也作了明确阐述。他说,“一般说来,兴趣就是乐趣”,它贯穿于人类日常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中。人类为维持和不断扩大自身存在和再生产的条件所作的努力,就是由兴趣促成和决定的。主客体的联系,最初就是借助于兴趣建立起来的。所以他把兴趣称之为“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以及与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条件--劳动和相互作用--相联系的基本导向”。这个基本导向“既不等于我们所说的本能,又不能完全脱离生活过程的客观联系”。
他反对实证主义把认识与兴趣相分离的观点,指出,兴趣先于认识,指导认识,是认识的墓础,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基础。然而,兴趣也只有借助于认识的力量才能实现。认识与兴趣的真正统一和融合,只能发生在自我反思的领域中,即发生在理论认识与追求独立判断或追求解放结合在一起的领域中。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认识兴趣决定了人的科学活动,而每一种科学活动又有它自已的特殊的认识兴趣。哈贝马斯把兴趣分为三种: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
技术的兴趣是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它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技术的兴趣是试图解决自然界的不可认识和不可理解性,是排除自然界对人的盲目统治。因此,技术兴趣也可以称之为有成效地控制自然过程的兴趣。技术的兴趣促成并决定者自然科学的恩想和研究。自然科学包含着技术兴趣;技术兴趣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墓础。
他把维护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以及确保人的共同性的兴趣,叫做实践兴趣。实践兴趣是精神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指导着精神科学的发展。“历史的解释学的科学包含着实践的认识兴趣”。
实践的兴趣给人类的历史的解释,目的是把人从僵死的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且“确保个人和集团的……自我理解以及其他个人和集团的相互理解”。
哈贝马斯阐述说,现实中,实践的兴趣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能畅通无阻。例如,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中,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机构对社会的全面统治,使对话受到压制,共性、共识已无法实现;相互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不可能,因而破坏了实践兴趣的发展。
解放的兴趣就是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其目的就是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女中解放出来”。按照哈贝马斯的见解,一切批判性的科学就是在解放的兴趣的墓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科学饱含着解放的兴趣。它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社会解放,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没有统治的交往关系和取得一种普遍的、没有压制的共识。
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的社会科学家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被意识形态歪曲的社会状况,甚至能够启发当代的政治活动家们对今后的科技发展和使用,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帮助他们扭转可能给广大阶层的生活造成危害的研究投资,他们应该成为治疗社会疾病的医生。
人类历史的前进与发展,首先取决于解放的兴趣,而解放的兴趣本身又决定于指导人们获取共识和拥有控制自然界的技术力量的兴趣。
通过对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三种科学(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的论述,哈贝马斯试图让人们认识到:在当今的发达社会中,技术的兴趣所创造的成果--技术,已经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了不幸和灾难;人们的实践兴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遭到了阻挠和破坏,人们达成的共识的涂径仍然受着掌握着政治和经济大全的少数人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解放的兴趣所指导的批判的社会科学,才能使广大阶层和社会摆脱物质匮乏和人际关系的紧张的困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试图重建的认识论是一种以自我反思为蒸础的、具有强烈社会性的,把认识与兴趣密切结合起来的、批判的社会认识论。他寄希望于他的这种认识论能造福于人们社会关系的改善。
哈贝马斯的理论著作晦涩难懂,这是他的读者公认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论题极为广泛:他所使用的语言带有德国哲学传统语言的抽象性和深奥性,还因为他在论述时大量便用了自己独创的新词汇、术语和概念。因此,读他的著作、译他的著作,需要付出数倍于他人的精力。英国社会学家彼得·威尔比把阅读哈贝马斯著作之艰难比之“奋力登山”。哈贝马斯的这种文风,甚至连德国读者和学者也感到不习惯,认为这是他的一大
“失误”。
标签: 微信表情含义图解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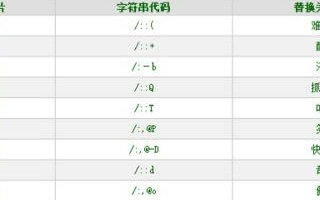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